作者:杨志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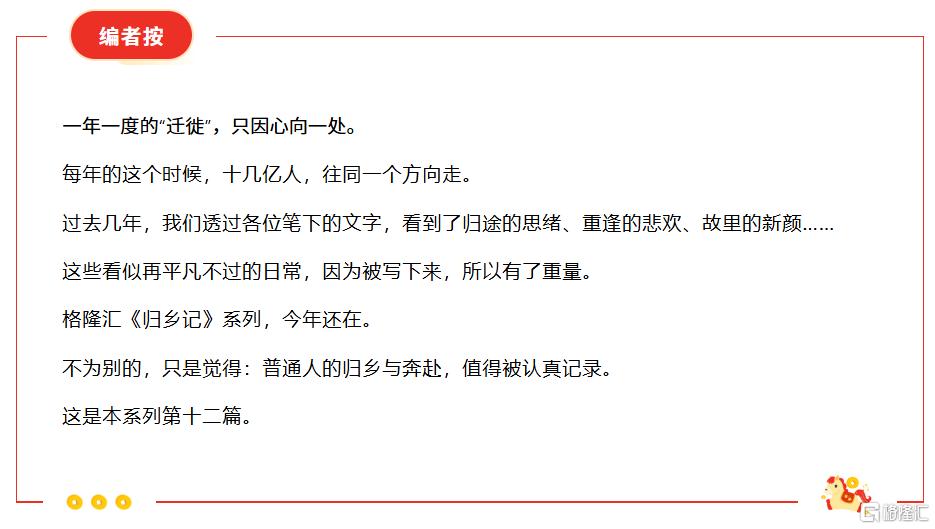
城市的灯火,是冷的。
尤其是腊月二十八晚上九点以后,高楼里透出的光一格一格,亮得规矩,也亮得疏离。张亮裹紧身上那件穿了三年、洗得有些发硬的黑羽绒服,缩着脖子从写字楼旋转门里挤出来。寒风立刻像找到了缝隙的贼,嗖嗖地往领口里钻。他加快脚步,汇入地铁口黑压压向下涌动的人流。不敢停,一停下来,骨头缝里积攒了一整天的、那种冰碴子似的疲乏,就会猛地往上一泛,让人只想就地瘫倒。
这种时候,他最怕的,就是口袋里的手机震动。
怕什么来什么。刚踏上通往站台的电梯,那熟悉又恼人的“嗡嗡”声贴着大腿炸开,震得他心头一紧。不用看也知道是谁。屏幕上,“娘”那个字,像个滚烫的烙印。
他盯着那个字,直到铃声快要断掉,才慢半拍地划开接听,把手机贴在耳边。地铁站里嘈杂的回音、列车进站的呼啸,和他自己有些粗重的呼吸,一起涌进听筒。
“亮子,”母亲的声音隔着上千公里传过来,带着电话特有的、微弱的电流嘶声,还有一丝……几乎难以察觉的小心翼翼,“没啥事,就是问问你……吃过晚饭没?”
照例的迂回。但张亮知道,下一句是什么。他喉咙有点发干,含糊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短暂的沉默,像拉长的橡皮筋。然后,那头果然传来那句他听了许多年、几乎能背出来的话:“那……今年啥时候能回来呀?”
声音很轻,甚至带着点赔笑似的试探,却像根针,精准地扎在张亮心口某个最酸软的地方。他张了张嘴,那句“工地忙,过年加班钱多”的托词就在嘴边滚着,却突然觉得无比厌倦。这厌倦是对这重复了无数次的对话,更是对他自己。
“娘……”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干巴巴的,像晒裂的土坷垃,“我……再看吧,还没定。”
“哦,哦,没定啊……”母亲的声音立刻低了下去,那点小心翼翼的期待像风里的烛火,噗一下灭了,只剩下惯常的、带着暖意却更让人难受的唠叨,“没事,没事,工作要紧。你自己在外头,千万吃好,晚上睡觉被子捂严实点,这几天看天气预报,你们那儿又要降温……”
背景音里,隐约传来几声空旷的咳嗽,还有电视戏曲频道咿咿呀呀的唱腔,在寂静的乡村夜晚,显得格外响亮而孤独。张亮眼前闪过老家那间堂屋,掉了漆的方桌,蒙尘的日光灯管,母亲一个人坐在小板凳上,对着那台旧电视的身影。父亲去世快十年了,自从他出来打工,那院子里,就只剩下母亲和她的影子。
他曾硬要接她来城里住过半个月。六十平米的出租屋,母亲手脚都没处放,总念叨着鸡该喂了,后院那畦葱该浇水了。夜里听见楼下夜归年轻人的喧哗和车声,她就整宿睡不着。最后,母亲执意回去了,临走时说:“亮子,那是根,得有人守着。你在外头飞累了,知道有个地方能落下来,娘心里才踏实。”
根。可他最怕回去的,就是这条“根”。尤其是过年。村里那些从小光屁股玩到大的伙伴,东子买了新车,强娃在县城开了店,就连学习最差的二狗,也靠着承包果园翻了身。只有他张亮,在大城市扑腾了这么些年,还是个流水线上的小组长,住着合租房,银行卡里的数字增长得比蜗牛爬还慢。
回去干什么呢?接受那些打量衣服牌子、试探收入、关心婚事的目光?听那些看似热络的问候底下,藏着比较、评判,或许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怜悯?然后,他的窘迫会成为家家户户火炉边、牌桌上最新鲜的佐料,被那些翻滚的舌头咀嚼出各种滋味。他受不了那个。所以,过去两个春节,他都用“加班”躲了过去,只是给母亲汇去一笔比平时多些的钱,仿佛那能买来一些心安。
“亮子?亮子?”母亲在电话那头提高了声音,“咋不说话?是不是累着了?”
“没,娘,我刚下地铁,有点吵。”张亮回过神,匆忙道,“您也早点歇着,别熬太晚。我……我再看看车票。”
最后一句是鬼使神差加上去的,说完他就后悔了。果然,母亲的声音瞬间明亮起来,带着一种不敢置信的惊喜:“哎!好,好!看票,看票!不急,你啥时候有空啥时候回,娘天天都在家!”那欢喜过于殷切,反而像块石头,更沉地压在张亮胸口。
他几乎是狼狈地抢着说:“娘,我进地铁了,没信号,先挂了啊!”
“等等,亮子!”母亲急急叫住他。他手指停在红色按键上方。
电话里安静了两秒,只有电流的嘶嘶声。然后,母亲的声音再次响起,却不再是那种带着讨好和期盼的语气,而是异常的平静,甚至有些冷硬,穿过嘈杂的背景音,一字一字,清晰地钉进他耳朵里:
“亮子,你怕的,不是村里人的闲话。”
张亮一愣。
“你怕的,一直是你自个儿。”
“娘……”他想辩解,舌头却像打了结。
“过了自己心里那道坎,哪儿都是家。过不去,躲到天边也白搭。”母亲说完,没等他反应,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。听筒里只剩下一串忙音,嘟嘟嘟地响着,空洞而执拗。
张亮举着手机,僵在原地。周围扛着大包小包、行色匆匆的返乡人流不断碰撞着他,他却像根柱子似的杵着。母亲最后那两句话,在他脑子里嗡嗡作响,来回碰撞。
我怕的是我自己?什么意思?我自己有什么好怕的?
他不明白。心里那团一直理不清的乱麻,好像被母亲这句话猛地挑出了一个线头,却更加缠绕了。
最后一班地铁呼啸进站,卷起一阵带铁锈味的风。他被人流裹挟着挤进车厢,找到个角落靠着。疲惫和困惑一起袭来,他闭上眼,想隔绝那些嘈杂,母亲的话却挥之不去。
“你怕的,一直是你自个儿。”
怕自己没用?怕自己失败?怕面对那个离开了故乡多年,却依然没能活出个人样的自己?
旁边传来带着浓重乡音的谈笑,声音很大,充满了简单的快乐。他睁开眼,瞥见两个和他年纪相仿的男人,皮肤黝黑粗糙,脚下堆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,沾满灰尘。他们正兴奋地讨论着回家的事。
“今年活儿不好干,没攒下几个钱,回去我娘肯定又得叨叨。”一个挠着头,嘴上这么说,脸上却满是笑意。
“叨叨就叨叨呗!”另一个浑不在意地一挥手,“只要人全乎乎回去,爹娘看见比啥都高兴!村里人说啥?说去呗!咱过咱的日子,他们嚼他们的舌头根子,谁还能把咱吃了?过年嘛,不就图个团圆!”
“对!管他呢!回家!吃肉,喝酒,睡到日上三竿!哈哈!”
两人相视大笑,那笑声坦荡而响亮,毫无挂碍,震得车厢微微共鸣,也震得张亮耳膜发疼。他看着他们被生活打磨得粗糙却明亮的笑脸,看着他们脚边象征着奔波与收获的蛇皮袋,忽然间,像有道极亮的光,劈开了他脑子里那团纠缠多年的迷雾。
是啊。管他呢。
别人怎么看,怎么比,怎么议论,那些飞短流长,那些无形的目光……它们之所以能伤害他,捆住他,不正是因为他自己先在心里竖起了一面镜子,时时刻刻照着那个自惭形秽的影子吗?他躲的,从来不是故乡,不是乡亲,而是那个不敢坦荡回去面对一切的——包括不成功的自己——怯懦的灵魂。母亲守着的老屋,从来不是需要他衣锦还乡的炫耀场,而是他无论何时回去,都能无条件接纳他一切落魄与不堪的、最后的退路和温柔乡。他竟然,差点把这最后的退路,也用自己的怯懦给堵死了。
心脏在胸腔里重重地跳了一下,然后疯狂地加速,血液轰地涌上头顶。他猛地站直身体,手指微微颤抖着,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屏幕的光映亮了他有些发红的眼睛。他几乎没有任何犹豫,找到那个刚刚拨过来的号码,按下了回拨。
响了两声就被接起,快得仿佛母亲一直就把手机攥在手里。
“娘!”他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沙哑,却异常清晰、坚定,甚至带着一丝久违的、属于儿子的任性,“我明天中午最后半天班,下午就请假去车站!今年,我一定回家过年!您等我!”
电话那头,是长长的寂静。静得张亮能听到自己如鼓的心跳,能听到电话里传来老家夜晚呜呜的风声。
然后,他听见母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,那气息通过话筒传来,有些颤,带着如释重负的哽咽,更带着淹没一切的、滚烫的喜悦。
“好……好!”母亲的声音终于冲破压抑,哭了出来,却又像是在笑,“回家!亮子,回家过年!娘等你!娘给你包你最爱吃的羊肉萝卜馅饺子!一直等着你呢!”
列车正在驶出站台,加速,窗外城市的灯火连成一片流动的光河,飞速向后掠去。而前方,是隧道,然后,是更广阔的夜色。夜色尽头,是故乡的方向。
张亮紧紧握着手机,贴着耳朵,听着母亲在那头喜极而泣的、反复的叮咛和唠叨。这一次,他没有再感到烦躁和压力。温热的液体毫无预兆地冲出眼眶,他仰起头,用力眨着眼,看向车厢顶部流动的光影,嘴角却一点点,一点点地弯了起来。
车窗外,流动的光河渐渐模糊,融化成一片温暖而湿润的光晕。
免责声明:所有平台仅提供服务对接功能,资讯信息、数据资料来源于第三方,其中发布的文章、视频、数据仅代表内容发布者个人的观点,并不代表泡财经平台的观点,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,仅供参考,用户需独立做出投资决策,自行承担因信赖或使用第三方信息而导致的任何损失。投资有风险,入市需谨慎。

 迁址公告
迁址公告
 古东管家APP
古东管家APP
 关于我们
关于我们
请先登录后发表评论